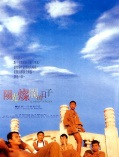
In the Heat of the Sun
(1994)
改编来源
《阳光灿烂的日子》改编自王朔的中篇小说《动物凶猛》。原著大概6万字,篇幅与内容本身很符合一部电影的体量。姜文没有动小说的整体架构,沿用了书中大部分情节。但影像与文字,表达方式截然不同。姜文用更适合电影的方法,“经济而又精准”地表述了大量文字才能传达的内容。[1][1]
音乐使用
《阳光灿烂的日子》没有原创音乐,整部电影中的音乐,是以意大利作曲家马斯卡尼的歌剧《乡村骑士》中的旋律和文革、苏联、朝鲜歌曲构成,成为本片的一大特色。影片里还出现了 《想念毛主席》、《友谊的花开万里香》、《卖花姑娘》 插曲、《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颂歌献给毛主席》等一系列极富时代特征的歌曲。[2][2]
演员选择
该片选角的第一要点不是演员的相貌长相,而是导演要在演员身上找到“感觉”,要觉得他、她(演员)就是“他、她”(角色)。第一个选定的演员不是夏雨,是演夏雨小时候的小演员,他叫韩冬,十岁左右。他让人有了无限的想像力,而且像是吸了氧一样,觉得整个摄制组的血液开始流动。
饰演米兰的演员换了几次,在确定人选后,导演姜文心里仍然犹豫。突然有一天宁静来了,她从前来过一次,姜文觉得她太甜蜜,个子又不够高,不适合饰演米兰。后来,有一天姜文在饭厅里吃饭,由于他是近视,没太看清,就感觉有个女孩子挺好的,过去一看,是宁静。这样,饰演米兰的演员又换成了宁静,虽然当时已经开拍。[3][3]
资金困境
《阳光灿烂的日子》在拍摄后期遇到的资金问题非常大:“前投资方撤资、新投资方观望”。姜文不仅要继续指挥剧组,而且还要四处讨钱拉投资。就在拉投资的过程中,原著小说作者王朔向姜文推荐了一个法国制片人Jean-Louis Piel,他在看完片后除了写下著名的“33条”意见书,还非常乐意解决姜文所面临的后期制作问题,这位和奥斯卡得主米哈尔科夫等人都有过合作的制片人答应替姜文去欧洲托关系找人,只要先给盘带子装上正片就好。然而,剧组当时穷的连转带子的钱都没有,姜文没办法,只好用家庭摄像机愣是对着剪辑机的画面拍了十多分钟,然后把这么一个“枪版”视频交给了Piel,“是,当时我根本没抱希望。”姜文回忆道。但很快,这位颇有神通的Piel联系上了金棕榈得主、德国名导施隆多夫,后者居然帮姜文安排到自己老家-柏林贝克斯伯格制片厂做混录。[4][4]
光效设计
姜文导演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采用了大量的自然光效,既满足了画面原汁原味的艺术性,又贴合了影片的光影基调:阳光灿烂。在外景照明中,最重要的是保持画面的真实性,导演在外景自然光的基础上,又给主角的面部加重了一个面光,与背景的光斑相映,不突兀却能突出主角的神态,聚焦观众视线,更好地将人物内心通过面部表情传递出来,强调了重点。影片中,太阳光线把北京胡同分裂成阴阳两块,这里的自然光运用得十分巧妙,在保持真实场景的条件下,赋予了画面更多的内涵,少年们燥热难耐的心情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相交融,少年们的炙热活力难以与之调和,而形成矛盾。内景拍摄时,在现有光线不足的情况下,可以借助人工辅助打光。《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出现的第一次人工模拟光源是在舞蹈室里,通过辅助打光模拟太阳光线照进室内,在屋内形成了梦幻的丁达尔效应,场景唯美动人,展现女性之美。[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