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ichael Gaston

演员(饰 Edward Balq)/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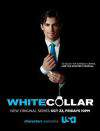
演员(饰 Thompson (unknown e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