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aruka Sugata

演员(饰 Miyako Kan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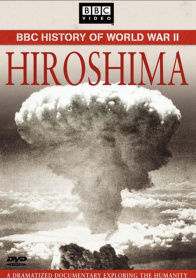
演员(饰 Aya Ana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