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演员(饰 Tomot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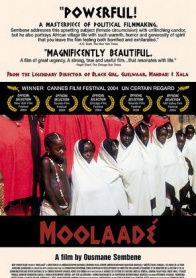
演员(饰 Ciré Bathily)/


演员(饰 Konat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