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imon Oakla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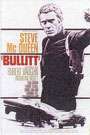
演员(饰 Captain Sam Bennet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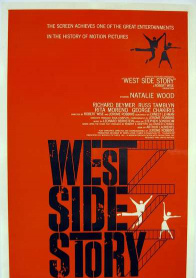
演员(饰 Lieutenant Schrank)/

演员(饰 Edward S. 'Ed' Mont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