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最后的夜晚》营销惹议 毕赣:余味定输赢
对话毕赣:能改变的叫遗憾 改变不了的叫命运
1905电影网专稿 西方形容幻灭:“发现他的偶像有黏土脚”——每日敬奉的神像是泥塑木胎。
5月份,片子赶上了戛纳。红毯上,和他一身黑西装,带着黑超墨镜的小姑夫相比,毕赣疲惫而局促。
直到媒体拍照环节,站在标有第71届戛纳电影节的白色台子前,白衬衫的李鸿其和蓝西装的黄觉之间,绿西装的毕赣才露出了一丝笑容。
那种笑是双手插袋,嘴角用力大于眼角,自在。
 |
| 毕赣与《地球》主演亮相戛纳photocall环节 |
7个月后,12月31日,2018年最后的夜晚。毕赣心情如何,我们无从得知。和戛纳首映欢呼相比,“地球”在内地院线上遭到的骂声让人错愕。
可能对于喜欢毕赣的人而言,最大的失望在于《地球最后的夜晚》与《路边野餐》的高度重复。
毕赣说,他害怕人们因为成功学喜欢上《路边野餐》。
那人们讨厌《地球最后的夜晚》,是不是发现,毕赣的成功学其实行不通?
对于一部投资高昂的文艺片——有消息称,制作资金达到了8000万——来说,收回成本已经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了。在为这部电影宣传的各种场合,毕赣的微笑仿佛神佛。
只是神像五指冲天摆,静默旁观,讲不出哲理。
壹
和《路边野餐》的酒店通告不同,《地球最后的夜晚》大量媒体采访,被安排在毕赣自己的公司荡麦影业。
这是毕赣电影里时空交错的地方,过去和未来的时间组成了这个乌托邦。
采访通告排得很密集。记者们在会议室和客厅分别架起机器,导演则在两边以20分钟为单位轮替。那些到早了的记者,被安排在制片人单佐龙的房间里等待。
虽然是制片人的房间,但却充满了毕赣的痕迹。桌子上放着印有荡麦的香烟,以及《地球最后的夜晚》中的道具——那张没有脸的女人照片。
一旁书架上挂着电影节的证件,戛纳、金马、洛迦诺,是单佐龙与毕赣的电影一起去过的地方。
灯很亮。不是毕赣在《十三邀》里和许知远聊到的那样:童年记忆里,住在澡堂边潮湿的房子中,醒来发现父母在吵架时会闪的灯。
在这样的一个舒适区里,毕赣并没有显得放松。他给那几天集中采访他的记者留下了几乎一致的印象——比起聊电影的实际问题,更喜欢聊形而上的东西。
和《路边野餐》时聊群演的病友奶奶、侯孝贤给自己的影响以及照顾自己的孩子不同,《地球最后的夜晚》毕赣面临的是回答投资、制作周期以及明星演员的问题。这些问题他可能已经回答到有了自己的标准答案,但每一家媒体仍在不厌其烦地问。
毕竟对于媒体来说,写一个只有两部长片的导演成长实在太单薄,不如写一写这部从开拍就秘闻不断的电影。
关于开机第一天的停拍,关于与演员的磨合,关于不断追加的投资。
如果没有口碑的坍塌,《地球最后的夜晚》像极了曾经那些艺术片大师们留下的传奇。属于毕赣的成功学可能就成为年轻人们参照的摹本。
贰
《地球最后的夜晚》在凯里开机后,曾有媒体试图联系毕赣的工作人员前往探班。但令媒体惊讶的是,工作人员的态度很警觉。事后回想,可能是那个时候片方就开始担心,媒体已经听到了电影停机的风声。
开机之后立刻停机,毕赣说,是自己和制片人没做好规划的原因。虽然有了公司,他拍电影仍然停留在自己的节奏上。
对于一部普通电影而言,经验往往是开机那天就要拍,摄影机不要停。“反正你拍两个月,三个月就拍完了,电影就这么结束吧,总不至于太差吧,那么多好演员在,那我偏偏就不想知道,我不知道电影应该按照怎么样一个正常的流程。”毕赣说,他不在乎流程的对错,但不是自己的节奏,就不要让他来拍了。
以毕赣的节奏,《地球最后的夜晚》预估投资400万,已经是《路边野餐》成本的40倍。当他把这个提案拿到金马的创投环节上时,许鞍华问他:“项目预算只有400万,你们的意向演员敢写汤唯?”
贾樟柯说,项目故事梗概已经这么敢想了,为什么预算却不敢往上提?
最后毕赣和单佐龙把“地球”的预算提升到2000万。
不是所有人都觉得应该按照荡麦的节奏做事。在那篇被转发了无数次的《“地球”的至暗时刻》中,单佐龙回想起开机那天的停机时这样写道:
“停机一天直接经济损失数十万,两个毫无工业经验的导演和制片,瞬间被击倒……
我近乎狼狈地逃回上海,准备第一时间向投资人阐明战况。深夜见到电影的主投方华策影业的傅斌星总,我磕绊颤巍地讲完情况,她却一直劝我吃小龙虾。我又试着给其他几家投资方电话通报,大家接到我的电话,都觉得我在开玩笑,怎么可能开机第一天就停机呢。
回到剧组,一片肃杀。”
在这一天前,黄觉已经在凯里生活了两个月。他减了20斤,然后学方言、熟悉地形,把凯里逛了个遍。
停机的25天里,片方换掉了与毕赣合作过《秘密金鱼》的台湾美术团队,紧急联系到《白日焰火》的美术指导刘强来救火。
毕赣说,停机的日子里,是演员在安抚自己。他“打打游戏啊,吃吃好吃的啊什么的,让自己快乐一点。”语气故作轻松。
但以剧组每天30万的开销来算,2000万投资里,将近40%打了水漂。
毕赣承认,也许3000万对于《地球最后的夜晚》来说最合理,性价比最好。但在他的眼中,追加投资后的“地球”,依旧是部很值当的电影:“因为工艺品质需要,工业需要资本一起去完成的。”
对于投资这件事,毕赣说,大部分时间是投资人在想办法帮他解决问题。他用人才培养做了个比喻:“如果在一家公司有一个人才,要培养一个人才花费的钱你们去看,真的想把他培养出来是花费巨大的。”
“所以我们再回到电影来看,真有那么多吗?真的有那么多吗?如果你从中真正学习的东西,那真的有那么多吗?也未必。”对于我们追问的投资问题,毕赣连着反问了三遍。
他对《地球最后的夜晚》很有信心,无论这种信心是来自于对自己创作的满意还是投资方收回成本的压力,他都把对自己第二部长片的信心毫无遮掩地展示给还没有看过电影的观众。
在一个探讨自己爱情观的沙龙上,面对一位观众“害怕花光钱拍电影却发现一无所获”的提问,毕赣这样回复:“不要害怕,你害怕只是因为你作品不够好,但凡够好,你为什么会害怕?如果你害怕了,打开自己的电影再看一遍就不会害怕了。”
观众问他,愿不愿意看自己的电影?毕赣一口回绝:“非常重要的是我看不看对你一点都不重要,我对你所有的建议都是无效的,我自己也从来不听别人的建议,所以我看不看不重要。”
台上远远望去,眼睛也像是没睁开的毕赣,说得也是这个时代最流行的“丧”鸡汤。
我对你没什么用,你需要寻找适合自己的运转规则。本质上就是与自己和解。
叁
在《路边野餐》刚刚上映时,毕赣还会谈及对自己作品的不满:“这一部资金特别少,一开始几万块零成本,我没有钱,要面对房间那么大的问题,我没办法解决这个事情,所以有太多遗憾。”
他也会直言自己的焦虑:在写剧本时,会因为写到特别好的地方而狂妄,又会在几个小时后开始自我怀疑。
但是在《地球最后的夜晚》之后,回看《路边野餐》,毕赣用更狡猾的口气说,《路边野餐》没有遗憾:“回去能改变的才叫遗憾,改变不了的叫命运,所以没有遗憾,只不过在制作电影的时候,我当然是希望它有更好的工艺品质。”
在和张悦然的对谈上,她也直言,毕赣给的答案比以前狡猾了。
让他显得略微真诚的,是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工作人员提示还剩最后一个问题的时间。那一刻,之前制造的某种气场被打乱,我们随便地问他,觉得从“野餐”到“地球”,自己有什么变化。
毕赣说,拍《地球最后的夜晚》三年里,自己没有了记忆。他所有的记忆都在片场,变成了一个制造记忆的人。
对于一个喜欢在电影里讲述记忆和时间的导演来说,这是件有些别扭的事。毕赣说,这三年里,自己回家变得难受,因为和家人没了过去细微的联系,反而变成一个空白的人。
“拍电影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挺矛盾的。一部电影三年就过去了,等于是你自己的记忆要有三年都是空白。而你制造出来的那个记忆,我都不知道它是好还是不好,我自己判断不了。”
从十几万元的低成本到现在的巨额投资,第二部电影有这么高的预算,是不是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毕赣的回答也很巧妙。站在当下回看3年前的自己,他否认《路边野餐》让他产生一种低成本的骄傲,坚持表示那时十多万就是一笔巨款。
拍《路边野餐》,毕赣说也是在对出钱给他的人负责,无论是老师还是妈妈。“地球”也是一样,他的任务是“要把电影拍到我想象当中的那个样子,追求到我能追求到的那个地步。所以关于艺术这件事情我会对我自己负责。”
唯一一次让毕赣激动的,则是在一个公开场合有人问到了《地球最后的夜晚》营销。这个问题也是毕赣在那天回答观众提问时说得字数最多的一个。
他是这样总结的:“从此他们观影几年里面多了一部电影,可能很难理解,就像看一幅绘画一样,等他们的生命经验发生改变以后,他们肯定不会想起其他的电影,肯定会想起我的电影,因为我的电影是珍贵的电影。”
在给我们的答案里,毕赣说了这样一句话:“余味定输赢。”
但电影现在的余味,对于毕赣来说,似乎是输了。和《路边野餐》的赞不绝口相比,喜欢《地球最后的夜晚》影迷变得少之又少。
一种制造记忆的人要被记忆埋葬的感觉。
可能和余味相比,毕赣现在需要的是第三部长片:改弦更张,重新定义。
关于这种状态,西方还有个说法:国王死了,国王万岁。是老国王去世,新国王即刻登基时礼仪上一定要喊出来的句子。
上一次人们迫不及待喊出来的时候,是《路边野餐》跳入眼帘。不少人迫不及待地宣告中国电影第八代导演的诞生。
这是这一次,可能埋葬的是毕赣本人,需要新生的也是毕赣本人。是一个年轻导演在经过资本洗练后,应该走向何方的故事。
在毕赣自己的电影世界里,国王死了,国王万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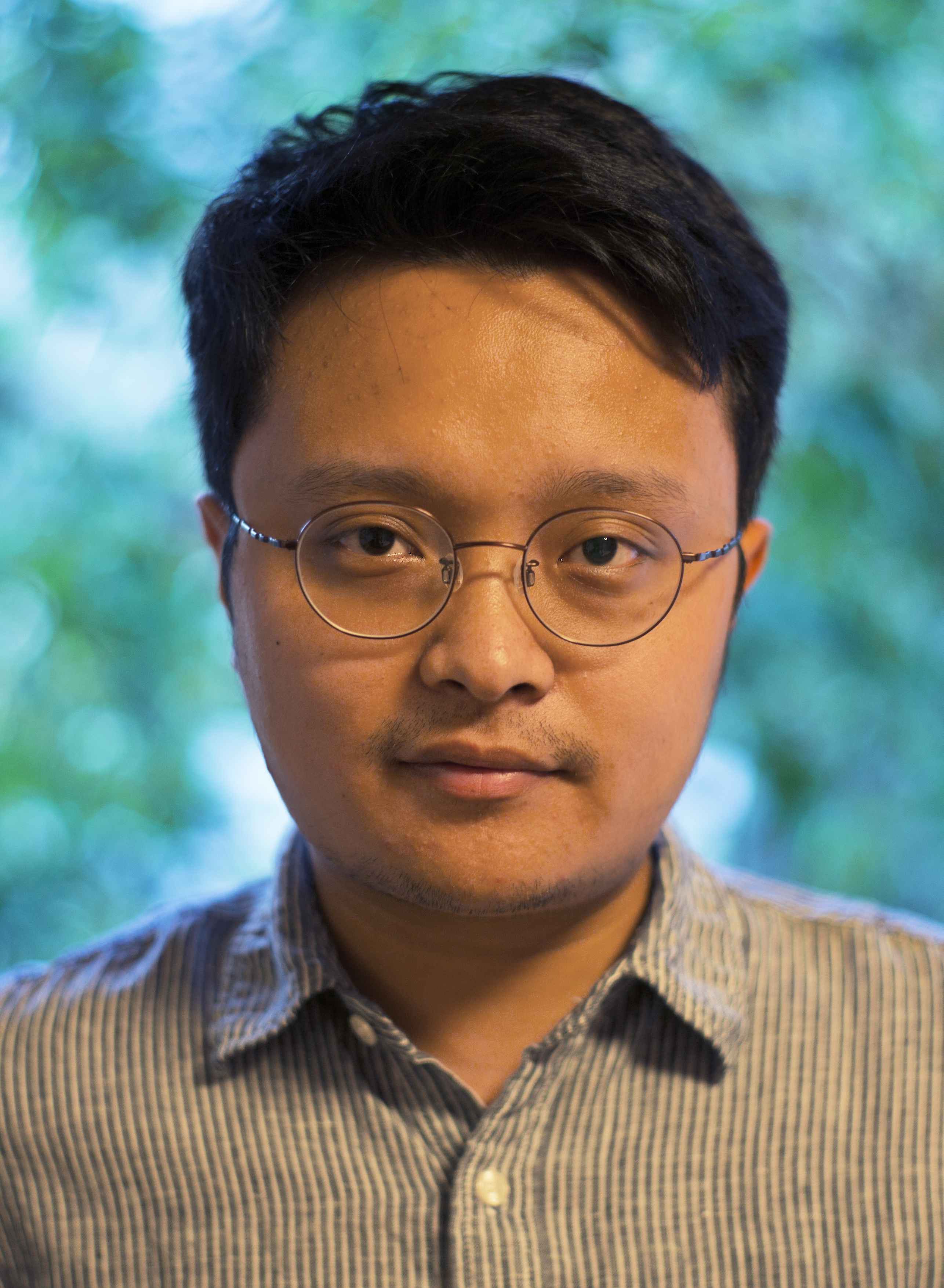
 杨紫李现领衔主演《锦绣芳华》收官,共彰唐风国韵美学体系
杨紫李现领衔主演《锦绣芳华》收官,共彰唐风国韵美学体系 宋茜陈梦同框晒合影!外出享美食互动温馨,心情大好状态佳
宋茜陈梦同框晒合影!外出享美食互动温馨,心情大好状态佳 张靓颖抹胸亮片长裙惊艳亮相:华丽优雅气场全开,尽显巨星风范
张靓颖抹胸亮片长裙惊艳亮相:华丽优雅气场全开,尽显巨星风范 微波炉煮鸡蛋藏风险!女演员遇爆炸受伤后发声提醒:别再这样做
微波炉煮鸡蛋藏风险!女演员遇爆炸受伤后发声提醒:别再这样做 电影《长安的荔枝》长春路演获赞“嘎嘎好看” 大鹏庄达菲刘俊谦分享角色代入
电影《长安的荔枝》长春路演获赞“嘎嘎好看” 大鹏庄达菲刘俊谦分享角色代入 姜文《你行!你上!》今日公映!五大看点奏响暑期档最强音
姜文《你行!你上!》今日公映!五大看点奏响暑期档最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