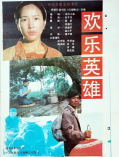
To die like a man
(1988)
编导伉俪首次合作
本片导演吴子牛与编剧司马小加于1983年结婚,而原著小说《风雨桐江》作者正是司马小加之父。吴子牛是中国第五代导演,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司马小加毕业于北京艺术学校钢琴专业,是北京交响乐团钢琴演奏员,两人的共同爱好是文学,《欢乐英雄》及续集《阴阳界》是夫妻俩第一次合作作品。司马小加介绍:“福建籍作家所写的较为有影响的长篇小说,一部是《小城春秋》,早已拍成电影;另一部就是先父司马文森的《风雨桐江》,反映的是30年代初共产党和国民党在闽南侨乡上上木、下下木及为民镇一带展开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我将它改编成《欢乐英雄》和《阴阳界》这两个剧本。不料,子牛起初居然怀疑我的水平,拒绝看我的剧本。殊不知我们几兄弟姐妹受父亲影响,自幼喜爱文学,我在搞音乐的同时,还到《人民文学》高级创作班和中国电影函授学院编剧班学习过。我逼着他看,他看了,说还可以,又改了一稿,终于在福建电影制片厂通过了,而且由子牛来导演。”吴子牛笑着补充:“小加写的剧本,阴盛阳衰,对女性、特别是玉蒜的心理描写很细腻,而我拍惯了打打杀杀的战争片,喜欢阳刚风格。这次拍的《欢乐英雄》和《阴阳界》也不例外,剧中的男人,从动作到肤色,都透出力度显示刚烈。但最终成果毕竟是我中有她!”
在编导合作中,夫妻俩求同存异。吴子牛喜欢影片有一种暴烈的风格,人说他拍的片子总有一股狠劲,司马小加却喜欢以细腻的手法,来表现闽南的地域文化。《欢乐英雄》对闽南神秘主义文化的呈现,一方面得益于小说原著对闽南民风民俗的书写和闽南地方文化自身的独特魅力;另一方面也有赖于导演和编剧的意愿与偏好。司马小加曾明确表达过对闽南鬼文化的执着,“我紧紧抓住闽南不放,我在做我父亲想做而没有做的事,是他使我与闽南结为一体”。吴子牛在执导的电影中也一直表现出对神鬼民俗等地方神秘文化的钟爱,对自然、世界的原初解释以及中国鬼信仰中包孕的集体无意识,都可以说是他独有的切入地域文化与国民精神的一个角度。如果没有导演与编剧对地方文化的特殊情感与独立思考,闽南鬼文化与电影的叙事和主题便难以如此相得益彰。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共同造就了《欢乐英雄》将地方文化融于电影的成功尝试,使具有普适性的人性命题能够在富有特殊性与强烈地方色彩的闽南文化中徐徐展开。
在人物塑造上,两人也不断碰撞出火花。如许三多这位下下木的农民首领,原著和剧本初稿都没有让他死,吴子牛这样解释电影中许三多的死亡:“许三多是中国农民的典型,忠厚但又愚昧,这样的性格注定了他的悲剧结局。于是,我就把他拍成先是千方百计买枪,继而自己动手造枪,而当他有了枪后,却在最需要枪的时候赤手空拳地死于乱枪之下。小加起初说我太狠,已经让那么多角色死了,还不肯放生一个许三多。可我觉得,只有赤裸裸地披露历史的真实,才能引起民族的思考和关注。也就是说,只有无情地让三多死去,从中揭示国民劣根性的危害,才能震撼今人的心灵,才是对今人、对观众的深情。”司马小加补充:“风水先生万正也是我俩共同创造的人物。原著中只有一个万歪,是富绅吴为民的一个略通风水却被人看不起的管家。我在家乡实地考察时却发现风水先生是很受人敬重的,于是灵感一来,改其名为万正,把他写成离间当地农民武装力量的阴谋家。”“这个万正写得好!我拍片时很注意处理这个人物,只是将剧本改了一处,即最后点明了他是长期潜伏下来的国民党中校特务,因为剧情发展到此,如果万正一个风水先生竟能策划同时扑灭两股农民武装的政治阴谋,那是不可信的。”吴子牛接话道。[1][1]